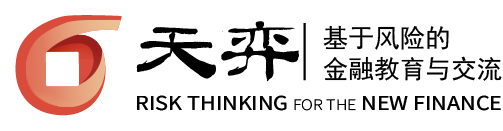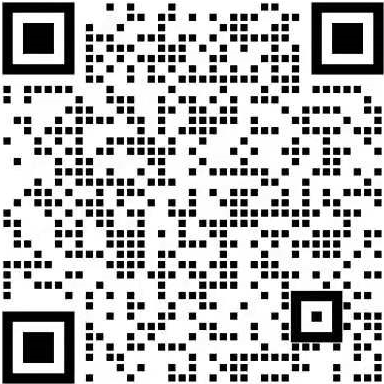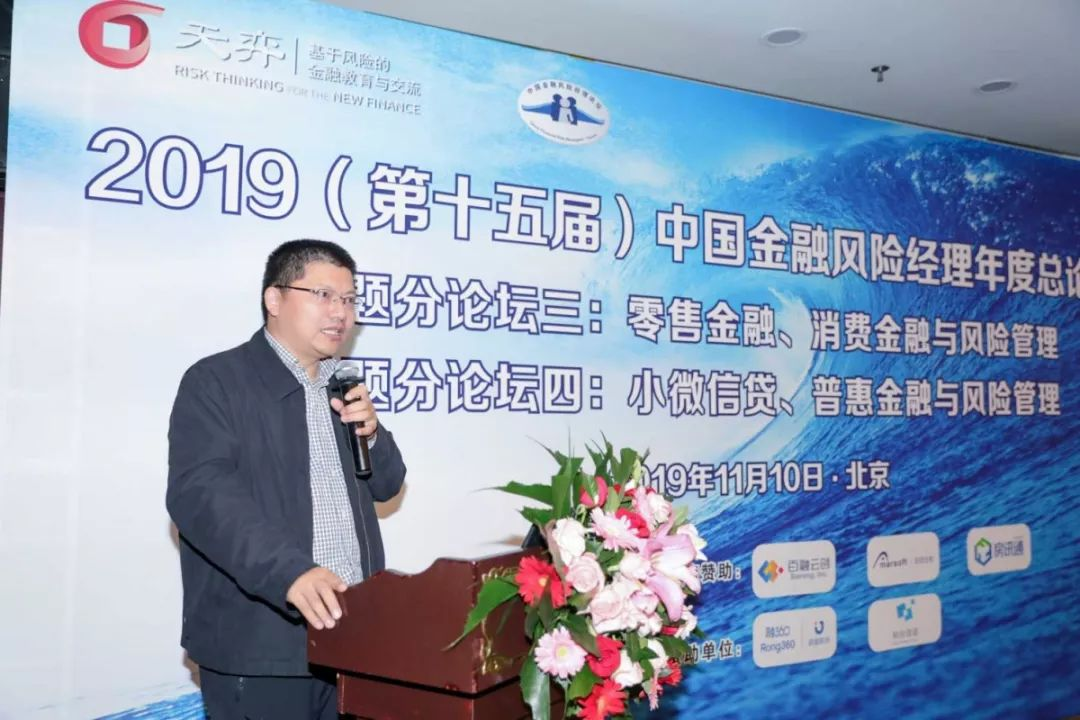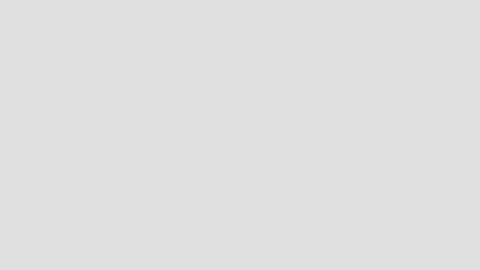
巴劲松
2010,分省投资与信贷关系中的“门槛效应”:审视投资增长的新视角,《金融研究》第05期。
2007,银行向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合法合理?,《银行家》第12期。
2005,我国资产证券化法制的现在和未来,《中国金融》第14期。
2003,信用涵义的经济解读和法律解读——一个比较的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04期。
2001,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发展走向,《当代财经》第03期。
2000,从法律角度看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代财经》第04期。
2000,中国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波动趋势,《世界经济》第04期。
2000,从法律角度看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上海金融》第03期。
2000,当前中国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波动趋势,《华南金融研究》第01期。
1999,现阶段启动我国经济的对策──兼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浙江金融》第06期。
1999,创业投资的运作机理及其在我国的兴起,《城市金融论坛》第04期。
1998,当前香港和新加坡金融界在香港指数期货上的争论及其演变,《青海金融》第12期。
1998,欧元启动的经济影响与我国经济金融界的对策思考,《浙江金融》第11期。
2010,分省投资与信贷关系中的“门槛效应”:审视投资增长的新视角,《金融研究》第05期。
2007,银行向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合法合理?,《银行家》第12期。
2005,我国资产证券化法制的现在和未来,《中国金融》第14期。
2003,信用涵义的经济解读和法律解读——一个比较的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04期。
2001,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发展走向,《当代财经》第03期。
2000,从法律角度看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代财经》第04期。
2000,中国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波动趋势,《世界经济》第04期。
2000,从法律角度看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上海金融》第03期。
2000,当前中国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波动趋势,《华南金融研究》第01期。
1999,现阶段启动我国经济的对策──兼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浙江金融》第06期。
1999,创业投资的运作机理及其在我国的兴起,《城市金融论坛》第04期。
1998,当前香港和新加坡金融界在香港指数期货上的争论及其演变,《青海金融》第12期。
1998,欧元启动的经济影响与我国经济金融界的对策思考,《浙江金融》第11期。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和逻辑
(一)三大支柱的逻辑
从监管的角度去理解三大支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第一支柱实际上是对重大风险以定量的方法进行计算,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
第二支柱是将第一支柱中没有覆盖到的风险以及覆盖不全面的风险,作为对于单家金融机构的额外资本要求,放到分子里来计算。第二支柱的本质是全面风险管理。
第三支柱的逻辑就是引入了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银行去强制披露自身的风险信息,这是因为监管机构的人员始终有限,这就需要大部分市场参与者来同时监督和评价银行,对银行的好坏进行区分。
(二)从监管角度看巴塞尔协议
它是一套规范,一套机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国际银行的监管标准和方法。首先,它是一个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形成了约束机制。第二,它以资本为抓手,去促进风险管理。第三,它以资本为枢纽,去平衡股东、经营层和存款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单体金融机构之间风险的关系。
它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任何银行都不能逃避监管,都要纳入到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范畴。
从巴I到巴Ⅲ的过程是资本充足率计算中分子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的过程。
2017年的《巴塞尔协议Ⅲ》是一个务实策略和技术原则的平衡机制。
(三)从银行的角度看巴塞尔协议
第一,巴塞尔协议要求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它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资产负债表上不同种类资产以及表外业务项目的风险及其资本充足率标准。第二,巴塞尔协议实际上是把风险计量、资本管理和业务管理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概念。第三,它提供了一个分母的激励机制,当银行选择更好的客户,有良好的风险计量技术的时候,那么同样的资本就可以做更大的业务。第四,它还是一个分子的约束,任何银行都需要有资本去支撑其业务以及风险。
从巴塞尔协议实施角度来看的话,它的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治理到政策流程的再造,再到风险计量模型的搭建、开发验证和审计,它是研发的一个整套的计量工具。
(四)带来的制度变革和技术革命
从监管的角度去看,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是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风险管理体制的变革;第二个就是它带来了风险管理的体系化;巴塞尔协议实施带来的技术革命是显而易见的,信息数据仓库的建立和先进计量技术的应用是做好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基础。
二、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我国的实施
从治理层面来看,巴塞尔协议的实施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第一个是模型的更新和迭代;第二个大的挑战就是风险管理和资源管理之间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甚至是多张皮,第三个方面的挑战就是风险管理和业务战略的脱离,如何把风险管理从一个事物层次到战略层次,从事前审批、事后问责,转向前瞻性管理、组合和全局管理,是这个层面所遇到的困难。
从技术层面可以看到,整个模型的哲学本土化和模型的质量有待提高,第二大的方面就是评级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从金融科技层面看,互联网的风控对于巴塞尔统计模型也会产生一些挑战。
三、我国资本监管的框架和要点
实施巴塞尔的资本办法的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合规层次,即满足它的最低资本要求,包括各类资本的要求,而且要对外进行信息披露。第二个层次是要建立一套风险管理的体系和架构,而且要注重风险权重与回报的平衡。第三个层次就是实施模型法,用内部模型去计量监管资本,把内部管理和监管资本的计量结合起来,但是这个需要监管机构的认可,一个基本的逻辑是:银行建立自己的模型,经过开发、验证、审计三道防线,模型上线后应用到各种不同的领域,包括评审、绩效考核各种不同类型的应用,当银行应用了一种循环机制之后,监管才认可其内部模型可以应用于风险资本的计量。
在巴塞尔协议实施的时候,监管的原则首先是希望解决“两张皮”的问题,一方面是把日常的监管和实施资本监管的要求进行融合。第二个原则是要处理不同的关系。
四、实施建议
从建议的角度来看,第一点是实施巴塞尔协议以资本为抓手的目标并不是为资本而资本,而是为了通过资本监管来推动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二点建议就是风险管理的治理和组织架构需要重构,而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
第三点建议是整个的风险管理需要制度变革和业务流程的再造,而不是仅仅引入评级就能解决,需要把整个信贷管理制度和评级制度融合在一起。
第四点是要注重模型的构建和后发优势。
五、资本推动下的金融机构转型
一是从规模导向到价值导向;二是从以前的账面利润到经济利润的转变;转变还包括以大论优到以质论优,从控制风险到主动管理风险,从单一的盈利到多元的盈利,从被动定价到主动定价,从一个部门制的银行到一体化的流程的银行,从比例管理到资本管理。
目前除了6家银行在实施内部模型法之外,也有不少其他的银行用内部模型进行自我管理,在这种自我管理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当监管的形势、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以后,一些优秀银行的内部管理所计量的结果也会逐步得到认可。
在巴塞尔协议进行变革的过程中,无论是监管标准更严,还是逐步转向市场,管理的逻辑依然没有变化,还是资本除以风险加权资产。在风险加权资产的风险权重的计量过程中,其激励机制也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鼓励银行去选择高评级的客户,选择有更多风险缓释的业务,让风险成本和资本成本变低,用同样的资本去做更多的业务,用资本去抵御非预期损失。虽然我国在实施的过程中会碰到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是依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来源:2020周末论坛《从监管角度看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我国的实施》